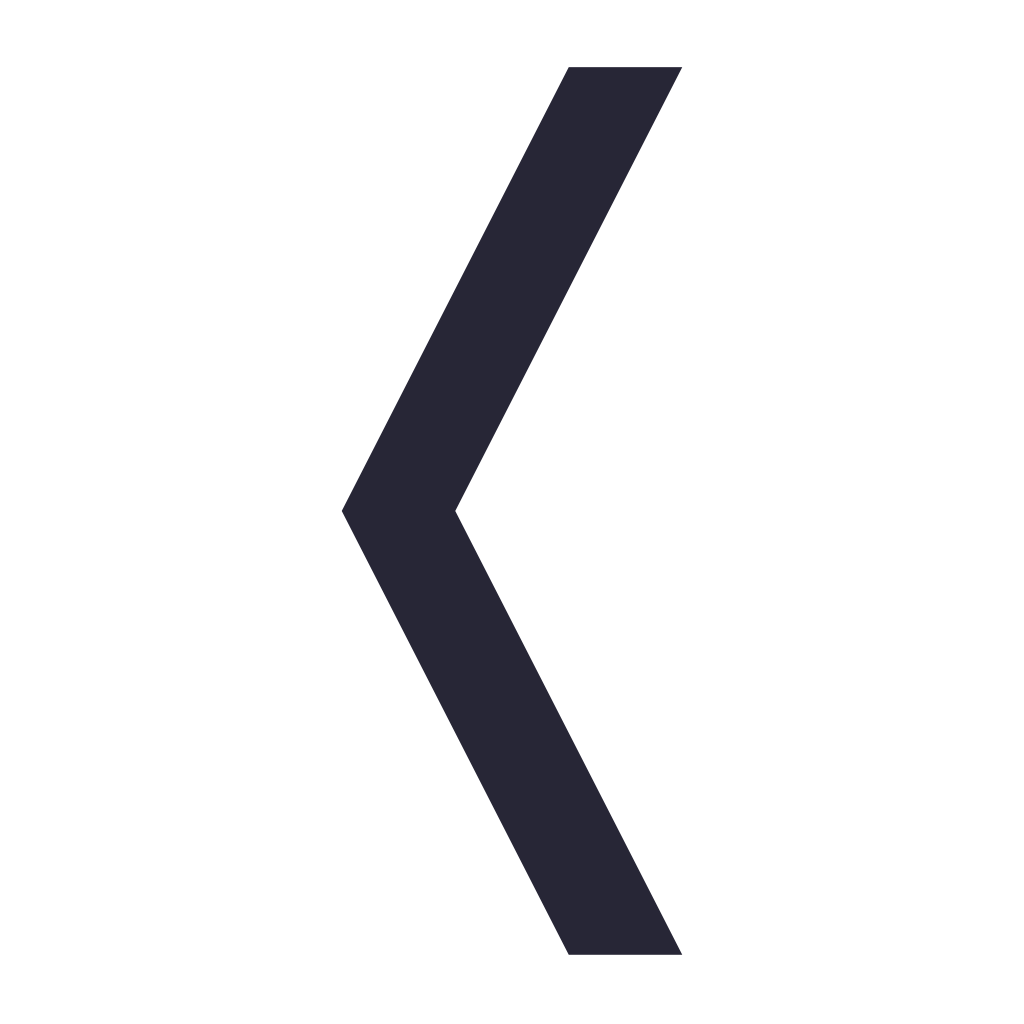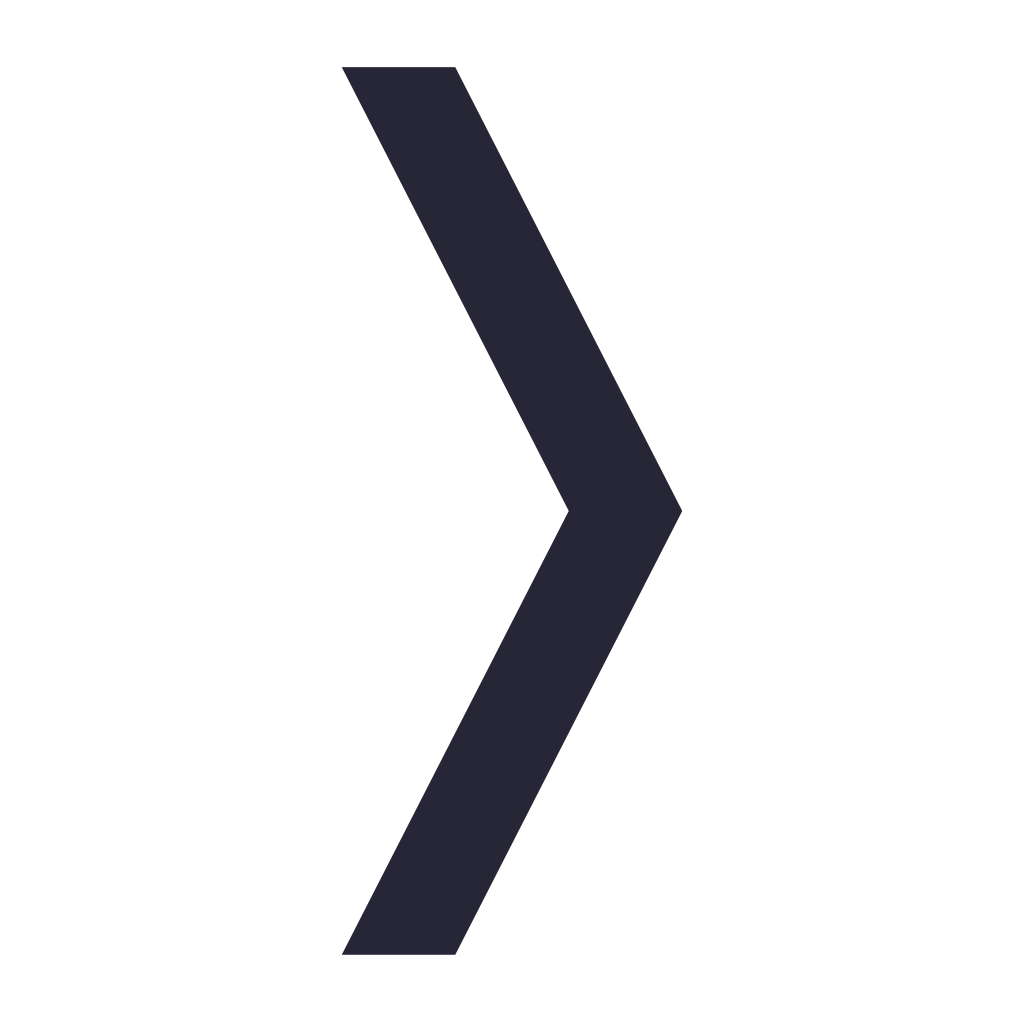余秋雨:口无恶言,自有另一种强大
本书是余秋雨的首部完整自传,深情叙写余氏家族百年间的悲喜沉浮。余秋雨首次正面回应20年来所有不实传闻:“深圳赠房”、“诈捐门”始末、与马兰的“被离婚”,甚至从未公开提过的第一次婚姻及其收养的女儿也在本书中做了交代。他史无前例地花费大量笔墨记述了马兰父母和马兰本人的经历。
姓余的人疼老婆
三年前,在上海的一家茶室,一位80多岁的韩国老人,满脸皱纹,但身板挺直,带着助理和翻译,出现在我面前。
老人立即就做自我介绍,他和我一样,也姓余。他急切地问我:“我们余姓,在中国怎么样?”
“人数不多,但也不错。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就有不少代表人物。”我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顶级诗人余光中,顶级小说家余华,顶级音乐家余隆,以及已故的顶级传媒人余纪忠……这些人,都是我的好友。
“我想证实一下,我们余姓的男人,是否有两个共同点?”老人严肃地问。
“哪两个共同点?”我饶有兴趣。
“一是倔。”老人说。
我想了一想,说:“对。”
“二是特别疼老婆。”老人说。
我立即轮番想了想那些同姓朋友的家庭,忍不住笑了,便大声地回答:“对!”
老人很满意,立即站起身来与我紧紧握手。
余姓,古代的历史线索比较模糊,好像是从秦代的“由余”氏派生出来的。反正历来不是大姓,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但是,余姓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族群,历来颇多纵横驰骋的脚印,因此,我更愿意离开谱牒排列,把目光放得广远一点。例如,公元13世纪余姓中所出现的奇迹,就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简单说来,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其中两个方面,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
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元史》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
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灭得很彻底,没有多少人活下来。据《西夏书事》记载:“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也就是说,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其他九十九个都死了。这活下来的一个,改姓了余。
奇怪的是,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1982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余氏族谱》上有这样两句诗:“铁木改作余姓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还说:吾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于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矣。
唐兀人改姓余,和蒙古人改姓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后来再改为余姓的。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对此,我的朋友、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余氏的形成和流脉,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只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余姓中极为重要的一脉,本来不姓余,也不是汉人,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改名换姓,顽强生存。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却能“一家生出万万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据调查,现在中国各地余姓的绝大部分,都与这一个脉络有关。而且,就精神气质而言,今天的余姓朋友,凡是身心比较坚毅,无惧长途跋涉的,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
离乡,上海读书
我读书早,九岁就小学毕业了。爸爸决定,还是要考中学,而且是考上海的中学。顺便,履行他婚前的承诺,把全家搬回上海。
从农村搬一个家到上海定居,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爸爸忙得焦头烂额。但他觉得其中最繁难的,是我考中学的问题。姨妈的态度最明确。她对爸爸说:“乡下那个小学我去看过了。秋雨到了上海应该先补习一年,然后找一所容易考的学校试试看。”
爸爸不太赞成,但又没有把握,因此急忙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要他到上海来与我谈谈。叔叔很快就来了。他穿得非常整齐,双眉微蹙,嘴却笑着,说:“现在辅导已经来不及了,还不如陪你熟悉熟悉上海。”
他本来想带着我去看外滩,但不知怎么脚一拐,走进了他每次来上海时必去的福州路旧书店。我第一次看到天下竟有那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
叔叔带着我在一排排书架间转悠。他不断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本书,放在我手上,给我介绍几句。我匆匆翻一下书,傻傻地问几句,又把书交还给他,他随手放回书架。开始时我问得有点害羞,后来胆子大了一点,问了不少。叔叔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又短又快。这天回家后叔叔对爸爸说:“他用不着补习了,今年就报考,找一个好一点的中学。”我是以高分考上中学的,这让爸爸、妈妈大吃一惊。
这所中学,对我来说,连每一个细节都不可思议。花岗岩台阶,大理石地面,雕花柚木楼梯,紫铜卷花窗架,窗外是喷泉荷花池。我怯生生地走进去,脚步很轻很轻。但是,我从来不在家里说学校里的事情。
有一天,爸爸问我:“你们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原来,爸爸的老同学、老同事吴阿坚的儿子吴杰,与我一起考上了中学。爸爸觉得,阿坚没有别的原因突然不理他,除非是两个儿子在学校里发生了矛盾。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吴杰,他也爱理不理。”
“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配。我分在一班,吴杰分在九班。”我说。
爸爸认为,这样分班是错误的,既会伤害学生自尊,又会制造嫉妒和对立。因此,他立即骑上脚踏车去了我们中学。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乐呵呵的。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会改过来。更让爸爸高兴的是,他终于知道了我的学习状况。他当着我的面对祖母和妈妈说:“我今天进校门,左边墙上贴着最新语文成绩排序,右边墙上贴着最新数学成绩排序,两边头一个名字是相同的。”他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听你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说,你还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上海北片数学竞赛第七名?”
妈妈笑着说:“这我就放心了。我原来担心他在乡下天天给人家写信、记账会影响学习。现在才知道,写信锻炼了他的作文,记账锻炼了他的数学。”我一直认为,我毕生的人生课程,主要完成于家办的“私学”,拥有两位最称职的女教师,祖母、妈妈。